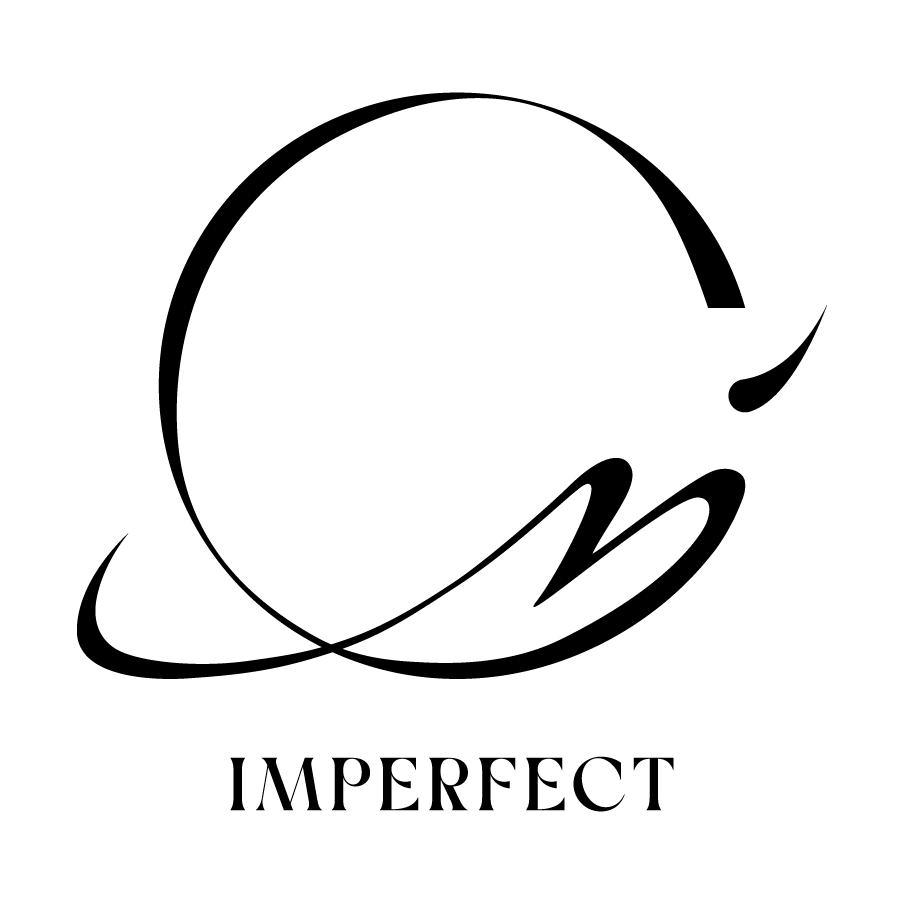捨棄名模身份,屬於戰地記者的創傷時代,在倖存後開始 ── Lee Miller
還記得在 Phoebe Philo 掌舵 Céline 的十年間,她是如何將極簡主義與女性剛柔並存的那面揮灑得淋漓盡致,其中的 AW14 系列,靈感除了來自於上世紀 30 年代的達達(dadaïsme)藝術家 Hannah Höch,還有傳奇戰地記者 Lee Miller,這次想要好好講述的故事主角。
「我會情願當拿著相機的那一個,而不是被拍的。」── Lee Miller
世上奇女子何其多,而 Lee Miller 算是當中特別剛烈的一個。名模、時裝攝影師、戰地記者、希特拉浴缸裡的女人… 這個予人感覺不安於現狀,志在打破界限的女人,在褪下種種社會所賦予的身份與名號後,剩低的卻是在前線戰場上見證過的各種地獄景象,還有倖存後纏繞她一生的記憶和創傷。
據外媒報道,她的自傳電影《Lee》會在今年開拍,記錄她從 1938 年到 1948 年由被攝者轉為拍攝者的十年人生,並由 Kate Winslet 擔起這位傳奇女子的角色 ,Jude Law、Josh O'Connor、Marion Cotillard 和 Andrea Riseborough 等知名演員亦相繼宣佈加盟。雖說要等到上映的那天似乎還遙遙無期,但在看過她的故事後,便不期然開始對這部傳記電影感到滿滿的期待。
生於 1907 年紐約的 Lee Miller,自小便擁有出眾的外貌,但在成為《Vogue》的模特兒發光發熱前的十多年歲月,她的童年卻只能用不幸來形容。七歲時被父母的朋友強暴並感染淋病,加上後來與父親之間那經已無從考究的種種傳聞所造成的心理影響,似乎預示了她注定難以平淡而安穩地度過一生。
人生的第一個轉捩點,在她 19 歲那年。差點被汽車撞上的她,因為湊巧被《Vogue》的創辦人 Condé Nast 救下,以此為機緣,走進了時尚圈的花花世界,每天被閃光燈包圍,成為雜誌封面的常客和無數男性眼中的靈感女神,更曾受邀演出電影《詩人之血》(The Blood of a Poet),扮演一個沒有雙臂的女人,看起來就像是那被譽為最美人體雕像的《米羅的維納斯》(Vénus de Milo)。
成名以後,或許是因為厭倦,也或許是想要擺脫那些總是灼熱的目光,她起了成為攝影師的念頭,毅然跑到巴黎發展,成為攝影大師 Man Ray 的助理和情人,也因此走進了法國藝術界的名流圈子,與畢加索和達利等藝術家打交道。看似順遂的轉型之路,她卻有感自己只是跳到了另一個被凝視的位置與角色,始終無法擺脫被男性評頭品足的境遇,感到渾身不自在的她,終在三年後選擇結束這段關係。
於是在男權當道的世代,她逐漸走上了女強人高地,在 1930 年代開辦了自己的攝影工作室,為 Gabrielle Chanel、Elsa Schiaparelli(當年讓 Gabrielle Chanel 忌憚及視為最大對手的時裝設計師,總用「那個意大利人」來稱呼她)、Virginia Woolf(被譽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先鋒作家,也是倫敦文學界的核心人物)等名留後世的創作者掌鏡拍攝,她們同樣才華洋溢,也同樣在奮力打破男尊女卑的舊有思維與社會現象。
後來 Miller 短暫嫁給了埃及商人 Aziz Eloui Bey 並遷居到開羅,離婚後,她與超現實主義藝術家 Roland Penrose 開始交往,兩人一同前往倫敦,而二戰的威脅亦在此時逐步襲來。戰火迅速蔓延,這時她再次選擇狠狠打破現狀,毅然成為戰地記者,隨美國陸軍走向戰場,先後見證了倫敦大轟炸、聖馬洛戰役、諾曼第登陸戰、巴黎解放等多場重大戰役,也成為二戰中唯一的隨軍女記者和攝影師。過去作為無數男人的靈感女神,大概從未讓她感到真正的快樂,她的驕傲,存在於執起相機的那一刻,也在於按下快門的那一個瞬間。
「方圓幾千里內的唯一一個記者,好像戰爭只是屬於我一個人。」── Lee Miller
戰爭期間,她在多個駭人現場按下了無數次快門,浮屍、集中營、集體自殺的副市長家族、廢墟上歌唱的女人… 但在她鏡頭下的影像,卻又莫名帶有一種詭異而超現實的藝術感,亦成為後世第一批公開的影像資料。但其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張照片,卻不是由她操刀,而是再次回到被攝者的身份。她在希特拉被美軍佔據的宅第浴缸中,拍下了裸上身的照片,充滿著揶揄意味,卻沒想到同日希特拉便吞槍自盡,於是這張作品成為了史上其中一張最著名的二戰照片,同時讓她被冠上「希特拉浴缸裡的女人」之名。
「戰地記者首先要成為一個超現實主義者,這樣生活中就再沒有什麼是超乎常理了。」── Roland Penrose
然而,從戰爭開始的那個瞬間,就註定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勝利者。即便是凱旋而歸的那方,緊隨勝利喜悅而來的,往往都是影響更為深遠的精神傷害。屬於 Lee Miller 的創傷時代,並非在戰爭的途中出現,而是在倖存後開始。那些慘像與恐懼,都化成了纏擾她一生的可怕夢魘。
「女性戰地攝影師必須在兩條戰線上作戰:炸彈和男人。」── Lee Miller
從戰場回來後,飽受戰爭創傷之苦的她患上了憂鬱症,過著終日抽煙和酗酒的生活,她放下了相機,與 Penrose 搬到英國鄉村隱居,將所有底片藏在閣樓,對過往所發生的一切隻字不提,試圖封印那些讓她痛苦不堪的記憶,就連她的孩子,也對她跌宕起伏的人生一無所知。直至她在 1977 年去世(享年 70),近六萬張照片才在遺物整理的過程中被發現,這位奇女子的事蹟也因而為後世所知。
晚年的她到底幸福嗎,後悔嗎,釋懷了嗎,我們無從得知,但她的剛烈、脆弱和勇悍,似乎能為這個戰爭再度頻生的時代,賦予點點的力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