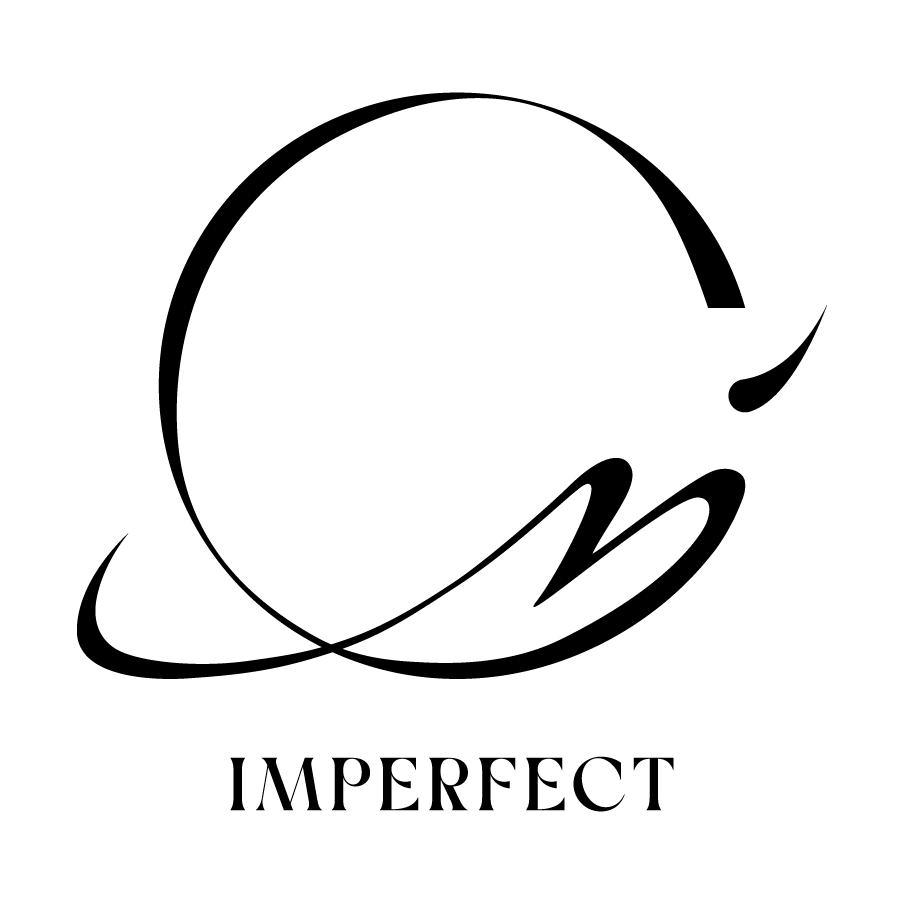文明世界的陰暗面:在灰燼大地與善惡共生 ──《草莓與灰燼》
好幾次在逛書店的時候看到這本書,卻遲遲沒有翻開的勇氣。那陣子察覺到對於生活的種種無力感,被壓得有點喘不過氣,於是我有意與那些過於沉重的議題保持距離,盡量閱讀一些輕鬆的內容,然後就因為看《SPY×FAMILY》時太投入被我爸一臉受不了地說我發出了很蠢的笑聲(沒記錯是次子暈船那集)。
好好清理了一遍積累已久的內在雜質,我終於翻開了《草莓與灰燼》,一頁頁揭開那些繁華表象之下的髒亂與混沌。房慧真筆下的草莓和灰燼,就像是光與影的存在,表面有多光潔,內裡就有多不堪。
以前在院子裡採草莓,一定要洗得很乾淨。祖母沒多說,現在他知道了,甜美的草莓上頭,恆常附著一層煙灰。
我總是會細細閱讀不少人都會選擇直接跳過的推薦序,通常只是出於想要順序並一字不漏地看完一本書的強迫症心態,讀畢後往往不會留下甚麼印象,但這次讀著楊佳嫻教授寫的序言,帶來的思考空間卻和正文不遑多讓。她寫道:「是否你我也在懵懂中洗去他人如洗去灰,心安理得吞吃甜豔草莓。我把〈草莓與灰燼〉當作情感教育,也當作倫理教育 ── 什麼是惡?什麼是庸常中的惡?骯髒與潔淨、人與非人,界線在哪裡?」庸常中的惡,或許是這幾年實在見過太多,想起那些披著人皮的妖魔鬼怪如何以正義之名四處作惡,讓我對這段話特別有感。
在災難前,文字無以描摹,彷彿任何描述都成了褻瀆,只能直觀地「看見」。
房慧真擅長描畫社會底層那些如同隱形般的邊緣人,而這本書同時也是關於劊子手的故事。她讀了大量關於納粹集中營、德國牲口列車、車諾比核災的歷史,她說二戰前的歐洲和被關進集中營前的猶太人,就像過去以東方之珠的姿態走在亞洲前端的香港,相對富足,有許多知識份子與社會菁英,卻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,一夕之間落入極端狀態,繼而萬劫不復。
也或許,文明所演進的繁華都來自犧牲,鏡頭聚焦至人們刻意無視的卑微暗處,被荒棄的不只是肉體,還包括倖存者的靈魂。
在那樣的時代之下,人性光輝與醜惡的一體兩面總是表露無遺,房慧真就特別談到了平庸之惡。「要讓普通人成為劊子手,首先要讓他們相信,要殺的不是人類,而是一隻可以踩在腳下的害蟲。」在人類的本能面前,文明有時會顯得脆弱得可笑,無論是為了自保而執起刀子成為加害者,選擇麻痺知覺的沉默者,都是誕生在平庸與日常中的邪惡,如同房慧真所說:「太陽越毒辣、世態越炎涼,隔著玻璃帷幕隔著電視螢幕旁觀他人的痛苦,誰也不想離開冷氣房。」,人類惡意的極大化,總是在文明世界特別顯眼。
一旦讓盡忠職守的人相信,他手上待處理的只是「物件」,而非有靈魂的人,齒輪便得以運轉起來。集中營裡的屠殺字眼不用「幹掉」(niedergemacht),而用「結清」(liguidiert),結清是商業用語,就像當今的網路購物,最後總會回到購物車結清、歸零,下次繼續。
另外,我也很喜歡〈煙花〉一章對於幾位年過四十但身心皆保養得宜的「老少女」的描寫,不結婚,不生育,學會了享受,也學會自愛,她們不再是那些年「姊姊妹妹陪上婦產科,宛如中學時手牽手上廁所」的傻女孩,如今對於情情愛愛,她們會像買賣基金那樣做風險評估,將不戴套又內射的床伴列為恐怖分子,從此拒絕往來,也不再倚賴運氣二字,四十八小時內走進藥房,說要買「那種藥」,氣定神閒地當場配水吞下藥丸,深明每個人到頭來也只有自己能對自己負責。她們偶爾也會自愛過了頭,比方說對家人的疏離與漠不關心,形成了一道無法被打破的璧壘。但對於她們來說,也唯有不被任何關係左右與動搖,才能保有平靜安穩的身心狀態。自愛或愛人,其實我們都不過是想要讓自己好過一點而已。
身體有了更形而上的層次,她們習慣這麼說,「做自己身體的主人」,誰不是自己身體的主人?什麼是「主人」?世事艱難,她們只想為自己的餘生負責,惡水上的小船,再也搭載不了任何人。
關於 房慧真
七○年代生於台北,長於城南,台大中文系博士班肄業,重度書痴與影癡。曾任職於《壹週刊》、《報導者》,獲調查報導新聞獎若干。著有散文集《單向街》、《小塵埃》、《河流》;人物訪談《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》;報導文學《煙囪之島:我們與石化共存的兩萬個日子》(合著)。數次入選年度散文選,以〈草莓與灰燼─加害者的日常〉獲 2016 年度散文獎。
photo by Sam Tso
produced by Ruby Leung
special thanks 誠品書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