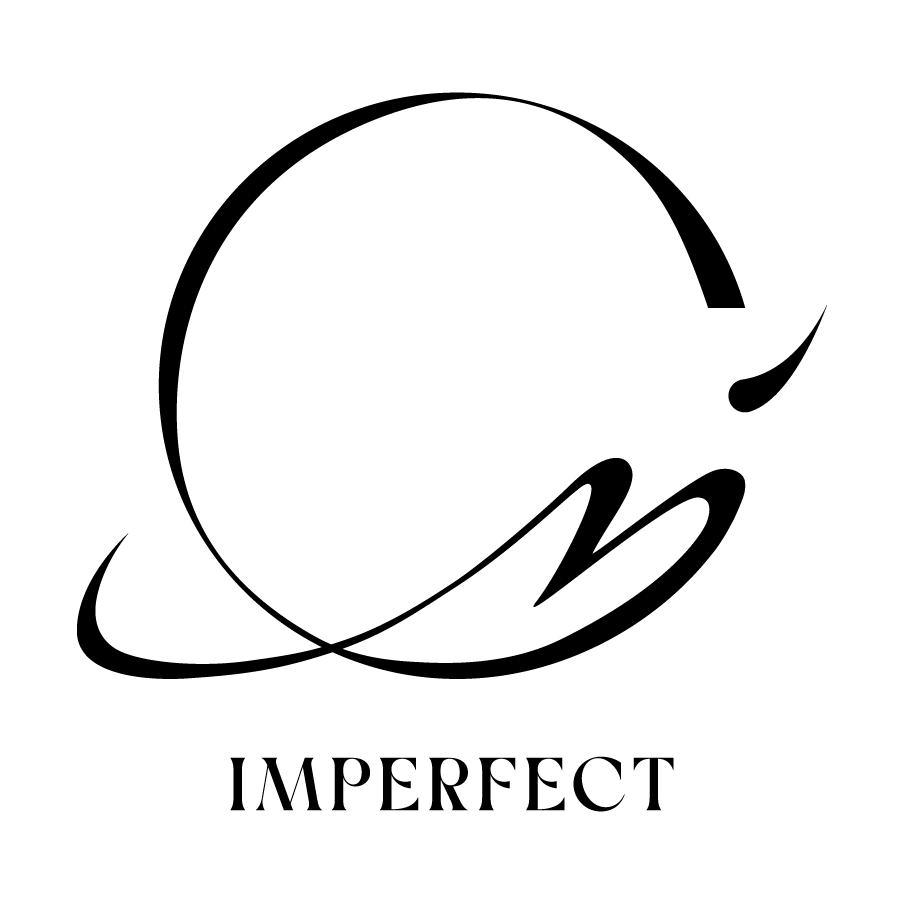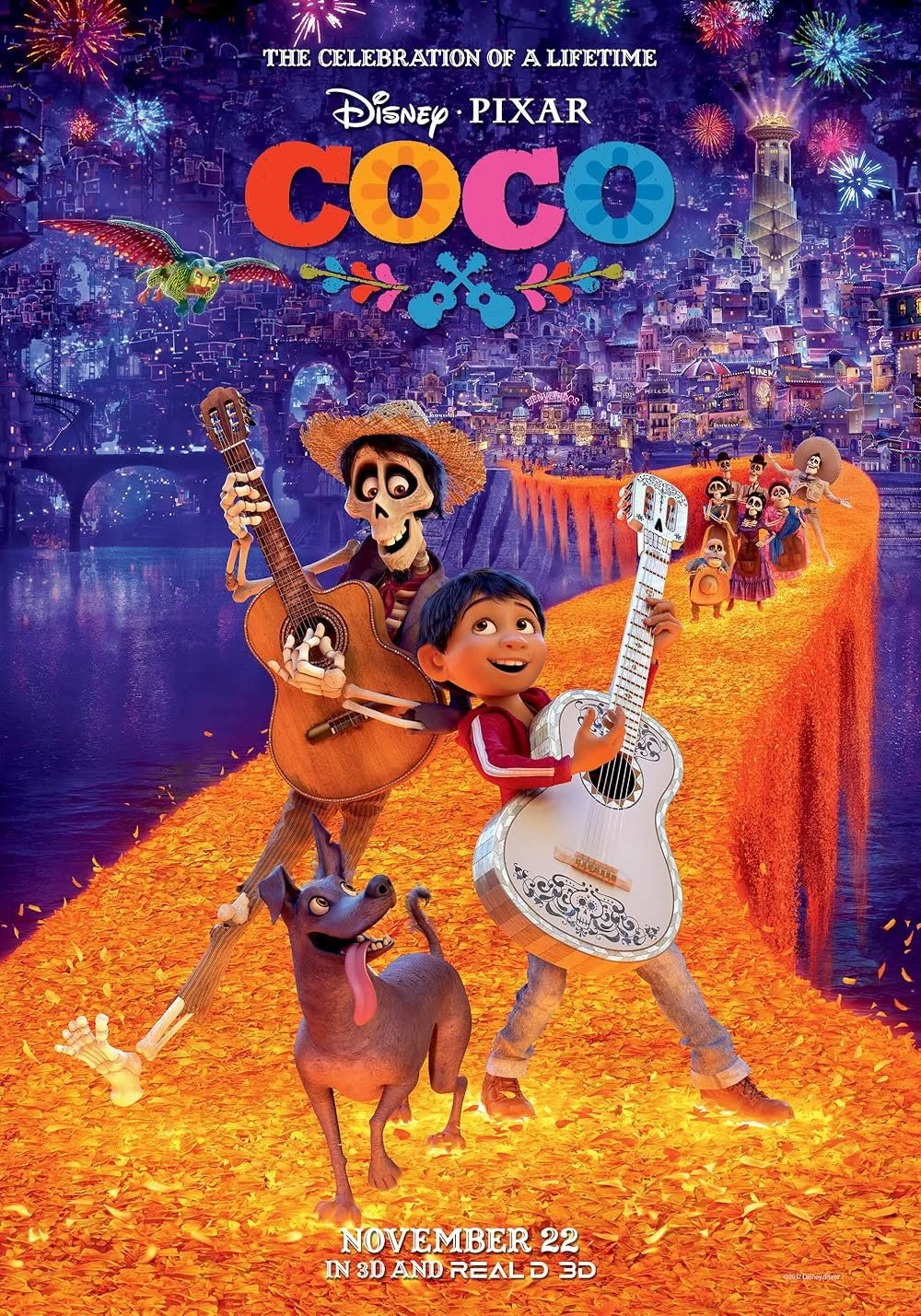死與生的雙向凝視,《Coco》中的記憶、遺忘、永恆
還記得,第一次看《Coco》的時候哭得有多慘。在墨西哥文化中,人有「三次死亡」,第一次是生理死亡(心臟停止);第二次是社會性死亡(葬禮後不被社會記得);第三次,是最終的遺忘,也就是世上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,都不再記得你。
電影以絢爛的動畫筆觸,將這個哲學命題演繹成一個由記憶構築的幽冥世界,亡靈們過著與人間相似的生活,卻又遵循著獨特的法則 ── 他們的存在,完全依賴於生者的記憶。
《Coco》中的冥界就像是人類社會的投射,被廣泛紀念的亡靈住在貴價高樓,享受著源源不絕的供品;被遺忘的亡靈則棲身邊陲地帶,只能等待自身逐漸消亡。他們掙扎著想要穿越花瓣橋,只為再看親人一眼,再聽一次自己的名字被呼喚。
故事中海特(Héctor)就是因為被誣陷而從家族記憶中抹去,成為遊蕩的幽靈。這似乎透露了,死後生活的質量,不僅取決於你是否被記住,更取決於你是如何被記住。因此,當米高(Miguel)開展穿越冥界的旅程,打破生與死的單向關係,並在最後為可可太婆(Mamá Coco)唱起〈Remember Me〉,他不僅是在挽救海特,更是在修復一個家族斷裂的敘事。
電影中最動人的部分,是對「終極死亡」的描繪 ── 當世界上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離去,你也將永遠消失。所以,存在的意義是否依賴於他者的記憶?如果無人記得,我們又是否真正存在過?
《Coco》給出的答案,既殘酷又充滿希望。它承認被遺忘的不可避免,同時又指出,通過愛與創造,我們可以延長記憶的生命。德拉古司(Ernesto de la Cruz)的音樂讓他被千萬人記住,但真正有價值的記憶來自真誠的情感聯結 ── 正如海特為女兒創作〈Remember Me〉,那份父愛穿越了生死界限,最終戰勝了時間與遺忘。電影中,照片、信件、樂器,甚至一首歌,都能成為連通生死兩界的媒介。當可可太婆抽屜裡那張被撕去的照片重新拼合,當海特的吉他再次被彈響,記憶的斷裂便得以修復。
死後的一百種生活,其實也是屬於生者的一百種記憶方式。通過有意識地紀念和傳承,在生與死的雙向凝視中,記憶成為對抗遺忘與虛無的有力媒介,請記住我,而我也會記住你。